官方配资平台 《史通》:刘知幾的所思所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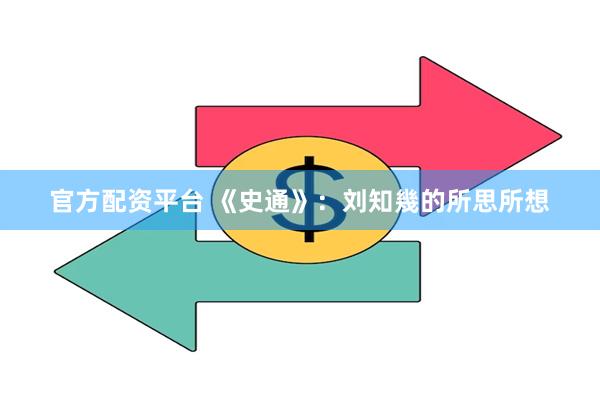
王嘉川官方配资平台
《史通》自问世之后,一直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。近代以来,由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更加突显,《史通》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。可以说,《史通》以其卓越的史学成就与贡献,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堪称不朽的经典之作。在《史通》中,刘知幾坦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,其学术思想表露得比较充分。
以重人事、轻天命为特征的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
刘知幾在《史通·杂说上》评论《史记》时,通过列举正反两方面多个事例,详细阐述了他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。在他看来,无论功业成败,无论国灭身亡还是坐登大宝,都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。他肯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主观作用决定的,并不是天命在事先主宰着一切。但他也认为,天命还是存在的,并随人事而转移。显然,他是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,天命是第二位的;既强调了人事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,也达到了宣扬“天予善人”,天命惩恶扬善的目的。由此可知,他不是不讲天命、不承认天命的作用,而是反对离开人事而单纯地讲说天命、推命而论。
展开剩余81%正因如此,刘知幾在解释历史现象时,皆能坚持以人事为主,不简单地归结于天命;对史书的内容,也强调不应记载与人事无关的“天道”,而要以人事为历史的中心,这在《书志》《书事》两篇中讲论得非常明确。但《书志》中也真真切切地大声疾呼:“灾祥之作,以表吉凶,此理昭昭,不易诬也”,因而对那些“事关军国,理涉兴亡”和“肇彰先觉,取验将来”的灾祥,予以记载,“其谁曰不然!”对灾异祥瑞的灵验很是相信。在《汉书五行志错误》中,他从八个方面,不厌其烦地批评刘向、班固等人对各种灾异与人事关系所作的荒谬解释,指责他们多滥、非精、无识,然后以真理在我的高高在上的姿态,重新将各种灾异与人事的关系一一作出解释说明、推演引申,“以所谓‘高深的’神学理论,驳斥别人庸俗的神学理论”。其强聒不舍、斤斤争辩的劲头,足见其对灾祥与人事相配关系的深信不疑。
很明显,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,“刘知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”。他的思想还处于一个矛盾的复杂体状态,虽然“基本上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传统”,但还没有达到无神论,是以重人事、轻天命为特征的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。
反对简单地以政治成败评论历史人物
《史通》这一历史思想的明显体现,是在《称谓》和《编次》中,通过反对以往史书不为更始皇帝刘玄设立帝纪并直呼其名的做法,明确反对成王败寇的正统历史观念。刘知幾在《自叙》中说,他在少年时就觉得范晔《后汉书》宜为刘玄立帝纪,后来读书益多,才知道东汉张衡也提出过这一观点。到三十年后写《史通》时,他将这一观点公开亮明,提出要把刘玄本纪列于光武帝刘秀之前,指出班固等东汉朝臣奉命纂修《东观汉记》,不敢如此书写,情有可原,但东汉以后的史学家如范晔,就不该再沿袭班固等人的做法,而应予以改革。显然,刘知幾是把他的观点作为千古不易之论来看待的,他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化身。而其立论的根据,只是刘秀曾经称臣于刘玄的事实,而把刘玄的失败、刘秀的成功完全抛在了一边,明显地体现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。
由于时代和见识的局限,刘知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,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持贬斥态度,不但动辄以盗贼、寇贼等蔑称相加,而且还因此反对将项羽列入本纪,在《本纪》中说“项羽僭盗而死,未得成君”,就算“羽窃帝名,正可抑同群盗”,批评《史记》将项羽列入本纪是“求名责实,再三乖谬”;同理,他也反对将陈胜列于世家,批评《史记》列陈胜于世家是个错误。与此相反,他对帝王将相表现出深深的艳羡和推崇之意,如《书志》中宣称“帝王苗裔,公侯子孙,余庆所钟,百世无绝”,要求在国史中立氏族志予以记载。这些论述,都凸显了他未能彻底地坚持不以成败论人的思想观念,是其阶级局限性的表现。
强调历史进步论
《史通》肯定历史发展中,古今是有变化的。《叙事》强调作者撰写史书要使用当时的语言文字,不可模拟古时古人的言语,以便“考时俗之不同,察古今之有异”。《烦省》强调“古今不同,势使之然”,认为历史奔腾不息向前发展,是古今变化的原因。《六家》指出:“古往今来,质文递变,诸史之作,不恒厥体。”该篇大旨就是阐明,一方面,随着历史的发展,逐渐产生出六种主要史书体裁及其流派,另一方面,因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,有四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这就从考察史书体裁发展演变的角度,强调了古今历史的变动发展的事实。紧接着,《二体》又指出,从三皇五帝到西周时期,文字记载简略,史书并无完备的体裁可言,只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,“载笔之体,于斯备矣”。认识到随着历史的发展,社会越来越进步,这就一笔否定了把上古三代说成是黄金时代的历史退化论,表现了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。
《史通》强调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同时,更要适俗随时,与时更革。《烦省》指出,早期史书全都记事简略,后来史书则记事详细,这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结果,倘若再以前人的简略为标准而批评后人的详细繁富,则“不亦谬乎!”强调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,不能以前人为标准,而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。《题目》明确反对设立书名和篇名时“习旧捐新,虽得稽古之宜,未达从时之义”的做法。《称谓》列举了一些史书对历史人物的称呼用语,然后指出:“凡此诸名,皆出当代,史臣编录,无复张弛。盖取叶随时,不藉稽古。”《摸拟》说“世异则事异,事异则备异”,《因习》说“三王各异礼,五帝不同乐,故《传》称因俗,《易》贵随时”,这都是强调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适时改革,与时俱进,推陈出新。
但适俗随时并不是要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,并不就是直接否定过去、否定历史。只有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,结合实际,应时变通,予以创造性地推陈出新,才能“庶几可以无大过”。
坚持以传统儒学思想为治史理念之本
《史通》的《疑古》《惑经》两篇,对儒家盛称出于圣人孔子之手的《尚书》《春秋》二书,从史学求实的角度,指出其记事不实的错误,称《尚书》有可疑者十条,《春秋》有不可理解者十二条、虚美者五条。但通观《史通》全书,刘知幾对这两部书还是以推崇为第一位的,是把二者定格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。
毫无疑问,《史通》的政治思想、是非标准,仍然是儒家所标榜的名教思想。在这个根本点上,《史通》并没有一点“非圣无法”的意识,它对孔子和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的批评质疑,只是从史书必须实录记事的角度进行的,并不关儒学思想本身。诚如当代研究者所言,刘知幾并不贬低孔子、轻视经书,相反,儒家经典是《史通》全书的主导思想,他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,认为儒家经典的地位远在史书、子书等之上,他在评论史书史家时,也以是否合乎圣人、经典之说为褒贬标准,并没有批判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,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,“他甚至有若干处指责《尚书》《春秋》所载不符合‘名教’,该隐讳而不隐讳”。总之,“知幾既不反儒,更不薄孔,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幾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。”
相对于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来说,在刘知幾这里,儒学名教观念是更高层次的、居于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,直书实录只是具体的行事准则;他所要求的直书实录,并不是无条件地进行的,而是在儒学名教观念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。在他身上,这两者并不矛盾,而是连体并生的上下辖属关系,儒学名教观念统摄着直书实录,指导着直书实录的进行,如果牵涉到名教问题官方配资平台,则自然是首先服从名教的观念。这是刘知幾的历史局限,是《史通》的不足,需要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正确看待,而不能苛求作者必须超越当时的主流思想状态。(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)
发布于:北京市
